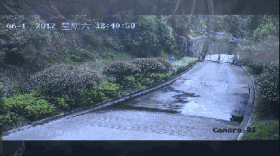事发现场

事发学校正门
杀机:贵州兴义学院杀人事件
龙仕绪仍然在逃。一场看似没有原因的行凶,一群自认没有未来的学生。在兴义这个贵州西南州偏远的小城,龙仕绪的杀机成为所有人都在探寻的问题。6月16日凌晨3点40分,“大二”学生龙仕绪从自己的上铺悄悄下床,走向宿舍斜对角的那张床铺,用一把西瓜刀很精准地在下铺郝进的喉咙上来回划了几刀,然后站在凳子上,轻轻地叫上铺韦辰的外号“小宝,小宝”。
挣扎
“声音很温柔,和他平时一样。”韦辰说。6月15日晚22点40分,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男生楼3、4、5栋,突然全体停电。“可能是线路检修吧。”同学们都说停电是突然的,并没有提前通知。因为学校电路老化,停电经常有,平时也没有熄灯的规定。这一天是星期四,按照本学期物理系的课表,他们整整上了一天的课,还有晚自习。平时晚自习必须上到22点10分才可以回寝室,不过这时已经临近考试,晚自习上不上查得不再那么严了。3楼307宿舍里的人都各自活动,谁也没和谁在一起。韦辰和李亮因为下午一起踢了一会球,都在停电以前就上床睡觉了。林月上床的时候大概是23点,他是唯一知道龙仕绪回来的人。他说:“23点过,龙仕绪回到宿舍。我们没说话。但当时郝进还没有回来。”
这间学生宿舍一共住了5个人。除了郝进,另外4个人经常在宿舍里打扑克,虽然不赌钱,但是一打就打到半夜一两点,郝进为此找过班主任老师反映。这件事是所有人能想到的郝进和龙仕绪最大的矛盾,但是当晚的杀机显然不是只针对郝进的。宿舍里有两张很破的小桌子,是共用的,龙仕绪用过的刀有一个刀壳子找到了,但刀子至今还下落未明。“是一把从来没见过的刀,大概30厘米以上,有点像西瓜刀,前面带弯度的尖。”韦辰说。
宿舍是长方形的,从门口走进去,右边两个上下床,门口这张是韦辰和郝进的,窗口那张是林月和李亮的,左边靠窗也是上下床,龙仕绪睡在上铺,下铺男孩叫陈然,去年已经退学,现在下铺就放了一堆大家的行李,左边还有一个六门的衣柜,男生的东西就歪七扭八地扔在里面,龙仕绪的柜子东西很少。床下也是放了几个纸盒子,还有就是足球、鞋子、书本。宿舍里都是农村孩子,还没有买电脑,课外书也几乎没有。“我们上网就去网吧,不过网吧还是贵,我们吃饭一个月六七百块才够用,实在没钱去玩。”
虽然门禁设在24点,但平时若回来晚一点,只要翻过三栋宿舍被合围的那扇铁门就可以,2米的高度,几乎驾轻就熟。在三个将要或已经入睡的人的记忆里,那晚实在没有任何异样,直到韦辰听到龙仕绪很轻声地呼唤自己。“龙仕绪叫我,我想是因为我的头一直朝向左面,就是朝龙仕绪站的这一边,他看不到我的喉咙,所以叫我是让我把头摆正。”韦辰应该还是没摆正,因为看不清楚的龙仕绪直接向他暴露的右脸砍去。
右脸先挨了一刀,刀口从耳朵直接砍到嘴唇。“我一点没感觉到疼,真的,有的报道说我一阵灼痛,其实我是后来缝针的时候才觉得疼得不行,我挨刀的时候只觉得很烫,因为血很烫,流出来了。”韦辰直觉反应是喊了一声。
紧接着就是第二刀,刀口横在脑门和头皮的交界处。“我只觉得谁拉着我的头撞上什么了。”这时的龙仕绪站在凳子上,正是韦辰的左边。韦辰顺手抬起了左手去抓住刀刃。“切西瓜的那种刀,前面是尖的,不知道他之前藏在哪里。”韦辰说,“我知道是龙仕绪,但当时他要要我的命,我们俩谁也没说话,稍微一松手就是你死我活了。”韦辰另一只手用力一推。
两个人从上铺一起滚到了地上。韦辰身高1.75米,龙仕绪1.76米,韦辰因为平时运动,还要有劲一些。“我只握住了刀靠近刀把的地方,前面还是往我身上砍。”但是韦辰已经用力推着龙仕绪,两人相持的力道即使跌落床下也依然保持,韦辰躺在地上,左手里一直握着刀不放,龙仕绪坐在他身上,刀尖在韦辰左肩上又划下两个很长的圆形刀口。
“我死命地推他,把他推倒了。我就赶紧背转身,去开宿舍的门。”宿舍门平时并不反锁,只有一个插销,一拔就可以开门,但是韦辰还在摸索插销的时候,左肩又挨了一刀,伤口大概有20厘米长。“这一刀还不算最重,因为我终于把门打开,右手一开门,往外跑,他向我的右肩膀,又狠狠地砍了一刀。”因为韦辰都在跑的状态,刀口虽然深而长,却都没有伤到筋骨。
韦辰一直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从郝进的床上传来,声音很大,“有点像水开了,又像是往水里吹起,噗吐吐的声音”。韦辰感觉似乎有人气喘不上来,这时他还不知道郝进已经被割开了喉管,只是拼命地向4单元自己好朋友的宿舍跑去,一路上血迹清晰。但当时楼道里一片黑,只有楼外的工地传过来的一点照明光。
死亡
林月和李亮这时才从梦中惊醒。“小龙,你搞廊子么?”林月在上铺对龙仕绪喊。“外面工地的光隐隐约约照进来,我能看见龙仕绪站着,他很平静地说不关你的事,随手拿了一个什么,不知道是包还是一件衣服,就出去了。他说话声音很平稳,我以为是谁从上铺掉了下来,因为他们谁也没说话,我就看见龙仕绪出去了。”因为龙仕绪的反应,林月觉得“有人做噩梦而已”。
这时候林月突然感到,就在自己的床头上方,郝进撑着床栏杆,站在那里,用手碰自己。“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指着自己的喉咙,然后就摸我的手,我一摸,全是湿的。”林月还不知道是血,他先和李亮打开了插电的小台灯,这才看见郝进已经趴倒在地上。“血在喷出来,声音很大,是气混着血往外冒的声音。”林月和李亮的第一反应是直奔4层和5层,因为他们班的男生大部分住在上面,只有他们一个寝室在3层。等到李学伟、吴向达他们进入307,“看见郝进全身是血”。
“他一直指着自己的喉咙,好像说很痛苦。我们几个人赶紧抬腿抬身子给他送到医院了。”李学伟说,“学校里很黑,我们连楼梯什么的也看不清,让一个同学赶紧取来手电。”郝进身上并没有多余的伤,也还有知觉反应。中医院和学校就在隔壁,人虽然送到医院了,却没有几个大夫在。护士只是拿纱布来给简单擦了擦,吴向达说:“都快5点了,才有安排让郝进进手术室,医生出来说,喉管食管都被割开了,在同一个地方不止一刀,当时拿了个单子出来,说‘情况基本稳定,不排除有生命危险’。”同学们以为这就是没事了,8点之前大家纷纷回学校上课去,学校第一节课没有上,派了老师来“通报这个情况”。到9点20分,医院突然传来消息:“郝进死了。”
大家都说郝进被杀了,“放气了,可是当时送到医院去的时候还没有人意识到是龙仕绪杀的人,大家只顾把郝进往外送”。一直到医院里,很快来了两个警察。“警察问我们,”林月说,“这么大事你们咋一点响动听不到?我们哪知道,真的一点也听不到。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是龙仕绪杀的人,他还回答了我一句不关我事,我没有把他和杀人联想到一起,他平时虽然不爱玩,但对人都很客气的。”到医院还有人说,龙仕绪怎么不在,有人说:“他不是有个老乡吗?可能在老乡那。”
李学伟后来在学校的监控录像里,看到了龙仕绪。“他翻过我们宿舍楼的那个铁门,手里拿的不知是包还是一件衣服,但人肯定是他,穿着白色上衣、长裤。也就是我们都在楼里救郝进的时候,等我们出来叫醒宿管来开铁门,他已经跑了大概有5分钟左右了。”这5分钟时间楼里的男生们特别是物理班的都聚在307宿舍,然后又全都去了医院,“楼道、宿舍院子,哪里都是全黑的,没看到什么人”。
韦辰跑到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好朋友张检的宿舍。“我当时没有穿鞋,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去的,反正我第一句话就是告诉他,不要开灯!”韦辰说怕龙仕绪在追赶自己,“要不是我这两条腿,我早就死得干干净净,说起来龙仕绪也不行,我要是他早把他弄死了。他根本追不上我。”韦辰的100米跑一直是全班第一,还是足球前锋,他说:“但是应急灯一开,龙仕绪就知道我在哪了。”张检说:“我们寝室没关门,他就直接跑到我的床前喊我,韦辰说,有人要杀他,我问他哪个,他说是龙仕绪,后来我想看他伤得恼火不,就准备去开灯,他说不要开,赶紧报警!我就报警。听到有人喊,我就看,看到是他们班的人,赶紧送他去医院。”
同舍
所有人都在回想,自己和龙仕绪有没有矛盾。而龙仕绪轻声呼唤韦辰的举动,使林月和李亮确信:“他就是要静悄悄地杀人,直接割喉咙。如果是特别激动,应该杀郝进就用很多刀,乱砍一气,怎么可能只割喉咙呢?还来回好几刀,没有一点余地。他不想吵醒大家。那如果韦辰也被杀死,下来就是我们了吧?”韦辰的说法是,郝进和龙仕绪平时有些小口角,“我还算我们宿舍最尊重郝进的,因为他们三个都有点瞧不起他”。
韦辰有点像这个宿舍的老大,虽然舍长是郝进,“因为大家都不想当舍长”。其实郝进在宿舍里过得非常不好,不过据说他谈过一个女友,只有他的床头贴着女明星海报。“他太内向了,没有朋友。”郝进的父亲说,“孩子从小连门都不爱出,也不和人说话,放假回来就帮家里干活。”郝进是纳雍人,农村的父母有四个孩子,三儿一女,他是最小的。“家里人比较宠爱他,一个月给他三四百元的生活费。”这个家庭一年的所得都是从土地得来,住在布依族聚居的山村里,四个儿女只有郝进出来念书了,其他人完全都在务农,没有打工。“我们有钱就给他寄一点,一个月最多要给他500块,有时候没钱都向人借了寄给他。”家里最大的开支,就是郝进上学,现在还欠了6000元的贷款。
韦辰、林月和李亮,虽然家里也是农村的,却相对来说经济条件要好一点点,一个月大约有600到800元的生活费。三人是狂热的篮球和足球爱好者,只要有空闲就往球场跑。家境相似又都来自毕节的郝进和龙仕绪一直有公开化的小口角,而且两个人从来不动手,都是嘴巴不好的。“尤其是郝进,不说话则已,只要是什么事情不顺他的意,他就要说些脏话,也不是直接说,就是嘴里不干不净地一直絮叨。我们都不喜欢他,我们宿舍经常出去吃饭,几乎没有带郝进去过。”
龙仕绪对郝进的反应比较大,有时候两个人都在宿舍骂脏话,却不正面冲突。“我们都是劝龙仕绪,算了算了。”龙仕绪是宿舍里年纪最大的,已经25岁,1986年出生,其他的人都在1988年左右。今年3月份,龙仕绪和郝进吵过架,当时龙仕绪在QQ里写道:“连他也敢欺负到老子头上。”所指应该就是郝进。龙仕绪和郝进都来自毕节,龙家在大方县长石镇杨柳村群益组,距纳雍还很遥远。他们到兴义来上学,完全是因为这个学校,专门负责给高考收尾。擦着“二本”线考进来的学生,没有人是直接报考了这个学校,几乎全都是因为学校招生名额未满,补录进来的。
龙仕绪的父母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没有来过兴义,从兴义到大方虽然只有500公里,然而山路蜿蜒难行,没有直达车,只能先回贵阳,再往大方走。同宿舍的几个人都是本省的学生,他们回家的车程大都需要10个小时以上。考来之前以为兴义是黔西南州的首府,“至少比我们那的城市要好,谁知道比县城还差,这所学校的所有设施还不如一个高中”。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学校,上世纪70年代建校是师范专科学校,里面还有一个乾隆年间的笔山书院的旧址,出过何应钦、刘培显这样的人物。不过现在的师范学院虽然从2009年开始转为公办全日制本科院校了,但是从校舍到教学还是显得落后。学校里面的几个楼房一层堆满了废弃物品,教师楼连下水道也没有,还是砖头房子。从里到外的看一遍,没有任何稍微体面的娱乐设施,布告栏里也没有任何有趣的社团活动或者讲座。学生们不是在运动场上玩命地释放过剩精力,就是在校园里外散漫地游荡。“本科用的教材是新的,很多专科教材还是70年代的,那书都卷巴巴了,图书馆更差了,书都是发黄的,我们都很少去。”尤其是学校的教学方式,自从2009年招录了龙仕绪他们这一拨学生,学校就在第二学期开了考研动员大会。原本26节课一学期,学校给加码到38~44节课一学期。早上7点钟上早操,晚上19点半开始晚自习,到22点10分才能走,每星期出操5天,上晚自习3天,老师点名,不到以旷课算,助学金大概十几个人能拿到,这些出勤率就是砝码。这所师范的学生补贴也很低,每个月20元打进饭卡里。
“学校当时说对我们这一级寄予厚望。”作为这种刚刚升本的学校,研究生入学率远远高于就业率的重要性。“当时招生说的就业率90%以上都是骗人的。师范类现在的就业已经饱和了,哪里需要那么多师范生,而我们的教学都是理论式的,可以说完全和外面不接轨。我们出来应该去教个中学,但现在中学也要研究生了,所以大部分毕业生都是去了私立的中学,工资待遇很差,也很累,根本谈不上教书育人。”吴向达说,“我们物理专业就一个班45个人,开学56个,退学了不少,这又没了俩,剩下的人,想考研的只有极个别。我们之所以来这所学校,全都是英语不行、数理化成绩还是不错的。但凡英语再高十几分,谁来这所学校啊?所以英语对我们全都是个最大的障碍。”学校的期待和学生的实力是两码事。
凶手
尽管在严密的高压之下学习,龙仕绪对学校和前途的看法显然比其他同学更加成熟。他在数理化方面有点天赋,“上课要么是看手机小说,要么睡觉,考前给他三天就都考过了,成绩还在中上”。自从龙仕绪杀了人,全体同学被警方和学校来回问话,把龙仕绪这个名字都从记忆里抹杀了,只说“凶手”。但一开始谁也转不过弯,吴向达说:“平时都和龙仕绪聊天吃饭挺多的,他不缺钱,也不问家里要,他都是靠自己带家教挣钱。别人带家教都要被家教中心压榨,带一节课100元,要给家教中心60元,但他嘴巴很能讲,家长有时候来了直接找他,高中那一套他还是很在行的。”一节课100元收入,龙仕绪一个月能带8到10节课,是班里的“家教大王”。
“一开学他穿的还是家里人给做的那种老布鞋,后来就开始穿‘美邦’了,不过所有的东西也都在一两百块钱。今年初他追过一个中文系女生,两个人纠缠一阵子,大概一两个月,没在一起了,他从那时起就变得很偏激了,整天喝酒,3月份有一次我陪他喝酒,他喝得胃不行了,到医院去输了两天液。可是他从来不和任何人说自己的感情烦恼,所以我都只是猜的,我们说话都是他让我说,他把我的想法听完了,都不说自己的。”物质情况好转,并没有使龙仕绪快乐起来。“自从恋爱失败,他就有点……总是说自己是从地狱来的,还是要回去。”
龙仕绪一点不内向,相反,他很喜欢和人讲大道理,显得很入世。“大一”的时候他还和同舍同班的人玩得比较多,一起去兴义附近的风景旅游区。不过他年纪偏大,很快就认识到了,目前的大学对他们来说实在只是一个空壳,“如果真要当中学老师,现在大学里学的也是一点用都没有”。班里的人一年就走了七八个,有重新高考的,上了四川一个地方二本院校,打电话过来说“简直是天堂,和兴义比起来”。龙仕绪已经25岁,经常自称“老头子”,“他觉得他肯定没法重考了,‘和你们年轻人不一样’,干什么都是浪费时间,最好能赶快去闯闯”。
“他从来不和我们打球,老觉得我们不干正事。”龙仕绪以自己的方式认识了很多外面的朋友,他以老乡、高中同学作为媒介,“连修电脑的、卖碟的、搞销售的,干什么的都认识,我们都觉得他交游广阔,不像个大学生了”。李学伟觉得:“这样肯定比在学校死读书好,读也读不出什么,都是农村子弟没有关系,公务员肯定要考,希望不大,只能靠自己去闯。”一谈到这种问题李学伟就和龙仕绪很有共同语言。“我们哪怕去打工,随便做什么,也比这样好,当个老师又穷又累,好学校进不去,还不如自己干点事情。”所以龙仕绪的务实反倒使他人缘很不错。“我们有事爱找他商量,谁的书丢了,他就去想办法,把退学的人的书弄回来。谁一时找不到家教,或是需要什么帮助,这种小事他很愿意主动搞,我们有时候都夸他能干,以后是能做大事的人。”李学伟说。
另一面的龙仕绪又很厌世。吴向达是同班同学里经常和他一起玩的,也是毕节老乡,他说“龙仕绪的手机铃声是‘大悲咒’”。龙仕绪喜欢表现得洒脱和深刻。“南摩惹纳达拉雅雅”,韦辰和其他两个同舍,一看到龙的QQ留言就知道,他又在把“大悲咒”里的字打很多遍。这些留言很多都是看似有点道理,其实很悲观的类似顺口溜之类的东西:“酒逢知已千杯少,马屁连天不嫌多。”“既然生活也苍白无奈,活着是一种惩罚,人间是地狱,我不是百毒不侵,你也不刀枪不入。”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诗词,都是表现生死的。“他总喜欢看玄幻武侠类的小说,里面有一些看起来很有道理又很玄乎的话,就成了他经常给人讲的。”吴向达说总是听他讲起那些话,“我们很少看,一般也不玩游戏了,可能他觉得玄幻小说里那些打打杀杀和纠缠的感情有意思,所以很痴迷”。吴向达说自己曾经劝他少看那些书,“但他觉得那些故事很有道理,有武功,有仇恨,有爱情,而且不用讲什么大道理”。
这种心理变化并没有引起同学的注意。龙仕绪和韦辰一个星期之前还在打牌,他说“但我确实很久没见过他笑了。而且龙仕绪最近总用一种很陌生的眼光看我们,还说觉得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完全没希望,都是群傻子”。李亮说:“男生之间也不会特别关心别人的情绪,我们都没有女友,郝进有,龙仕绪谈了一个没成,但是在宿舍我们不说这个,主要是不想和郝进说话。”比起宿舍同学的简单,龙仕绪更偏爱和校外朋友在一起,也是因为可以不用再故作大学生的矜持。“我觉得他不像个学生,他说话很老练了,在社会上的人都觉得他不是个‘菜鸟’。”他的老乡徐辉就住在师范学院外面的出租房里,一个月150元,狭窄又不卫生,并不比宿舍好,可是龙仕绪十分喜欢来找徐辉。“我不在他自己有钥匙也来呆一会,他一直觉得自己会成功的,可是却什么都懒得做,就躺在床上看玄幻武侠。”徐辉说。
徐辉已经毕业了,自己靠着打点零工的收入,找工作四处碰壁,他说:“龙仕绪杀人我到现在还是不信,他平时连动都懒得动,他跑了就没再联系我。其实我的想法比他还偏激,但我只是想想而已。龙仕绪的哥哥在部队里原来是个日语翻译,军校毕业很光荣的,他说他觉得哥哥是牺牲了,但家里那边都说是病死的,反正哥哥死了他们家就失去了希望。他也是考了好几年,才上的这个学,拿哥哥的抚恤金来读书,他却觉得太不划算了,这个学上得太失败。这两年学费的助学贷款,政府也发给他了,学校发的助学金,也有1000多块,他倒不太在意,老是说让同学们不用照顾他。我觉得他不大在意物质,但是也偶尔买点彩票,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干点大事。”徐辉还是不相信龙仕绪那么残忍而冷静地杀害别人,他说:“他一直和我说他信佛,最近半年他都说他在学佛学,我说为啥要学,他从手机上翻出一句话:‘杀身取义,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