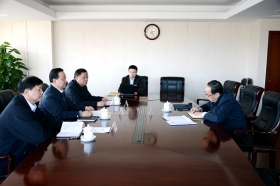在拥有89户人家的弄别寨,有近30户的男子娶了缅甸老婆,他们依靠活跃在各个寨子里的媒人牵线搭桥。在云南长达4000多公里,充斥着战乱、毒品、流行性疾病等问题的边境线上,弄别这样的寨子不是个别,“亮”这样的婚姻中介也不止一个,而边境婚姻似乎被忽略了。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李元涛 摄影·李进红
“亮”,一个46多岁的傣族妇女,住在瑞丽距离中缅边境不到5公里的寨子里,看着忽然而至的陌生人。她异样的眼神告诉我们,自己最近有不少麻烦。
缅甸女孩“也瑞”的出走是“亮”成为被告的主要原因,来自大理的原告尹万桥一家认为,亮和另外3个媒婆串通缅甸女孩也瑞骗婚,从中牟取婚约款16500元。
“亮”否认她欺骗原告,最直接的证据便是她所居住的弄别寨,89户人家,其中30户娶了缅甸老婆,他们虽然没有结婚证,没有中国国籍,但绝大部分过得幸福。
尹万桥急于找一个媳妇,中介从缅甸找来女孩相亲,双方明码实价。尹万桥的相亲经历更像是一桩“买卖”,到底谁在这桩“买卖”里面犯了错,导致交易失败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但媒人为了拿到相应的报酬,发现问题后仍然极力撮合双方;而尹家为了娶到媳妇,把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外国女孩带回了大理。
当然不仅仅这些,云南长达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越南、老挝、缅甸分别与中国接壤,中国必须面对复杂而充满变数的边境问题,其中包括婚姻。“亮”这样的婚姻中介不止一个,弄别这样的寨子也绝不是个案,但在这条充满斗争、战乱、毒品、流行性疾病等问题的边境线上,隐藏于民间的婚姻状况似乎被忽略了,他们当中,极少有人会领到结婚证,更别谈居住权问题。
新娘跑了
“在瑞丽这边好找媳妇。”2007年12月,26岁的大理人尹万桥通过堂兄尹义得知,到瑞丽可以找到媳妇。随后,尹义找到了当地人“应”帮忙介绍,“应”接下这单“生意”后自觉难以完成,又联系上当地有名的媒人吞亮、喊勐和亮三人共同给尹万桥找媳妇。
不到一个月,媒人就通知了尹义,让尹万桥赶快到瑞丽相亲。“没想到会这么快,更没有想到是缅甸姑娘。当时还只是想从瑞丽当地找一个。”尹万桥的四叔杨丙忠说,媒人把姑娘带来后才知道是缅甸人。
“先看了第一个,但是人家不满意,走了;也瑞是他看的第二个,双方同意才带走的。”媒人之一的亮说,她觉得尹万桥有点呆,所以第一个没有看上尹万桥,后来也瑞还是在她们的极力劝说下才同意的。
就这样,尹万桥和他的家人在没有和缅甸姑娘也瑞做任何交流的情况下,由其四叔杨丙忠垫支了16500元的婚约款,并与媒人签下了保证双方完婚的保证书。“一家人都很高兴,带着也瑞去买衣服、首饰,家里人还是很喜欢她的。”杨丙忠说,给也瑞购买各种衣物又花掉了近3000元。然后带着也瑞回到了大理。
“请帖发出去了,酒席也准备好了,第二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准备办他们的婚事。”尹万桥的四叔杨丙忠说到这里有些无奈。2008年1月4日,也瑞在结婚前一天,拿走尹万桥的身份证,借着上厕所的机会逃跑了,留下尹家人去挨户退请帖。
杨丙忠随即追回瑞丽,在当地弄岛派出所报案,要求几个介绍人退还他们婚约款16500元。经当地派出所协调,被告方共退还了3800元,其余部分他们不愿承担。去年6月,杨丙忠将也瑞和4名媒人告到了瑞丽市法院。
“你们帮我问问,法院什么时候才能开庭啊,如果不能的话我想把钱退回来。”一年过去了,繁琐的涉外婚姻法律程序让杨丙忠几乎想放弃用法律手段解决此事的念头。
和尹万桥家一样,媒人亮在等待中感到了不安,她希望早日作出处理,这样可以安下心来做其他事。“我就拿了500元的中介费,已经退给他们了。”除此之外亮还被罚了款。她说,也瑞离开尹万桥主要是因为尹有精神病,到大理之后经常被尹万桥虐待。也瑞出走时还得到了尹家亲属的帮助,要不然也逃不出来。
杨丙忠否认了亮的说法。他说,尹万桥老实,不爱说话是真的,但绝对没有精神疾病。“去大理之前,我还问过姑娘,如果不愿去,现在回去也可以,但是她说她能够呆下去。”杨丙忠说。
双方各执一词,也瑞也早已经回到缅甸,再也没有露面。“这种案子很麻烦,缅甸姑娘已经跑回去了,而我们不能跨境去递交起诉书,只能在国内进行公示,而这个公示期必须满半年。”瑞丽市法院民庭俸桂仙庭长说,尽管公示期很长,但一般情况下主要被告、缅方的也瑞很可能不会出席庭审,判决生效后的执行也非常困难,所以判决很难终结双方的纠纷。
结婚与买卖
“中国媳妇太贵了,那边的便宜,所以都喜欢到那边去买。”衣和亮同是弄别寨子的人,他4年前找了缅甸媳妇井,两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当说到为什么找一个缅甸老婆,“便宜”二字脱口而出。他说,在中国的寨子里找一个老婆至少要1万多元的彩礼,而他娶了缅甸老婆仅花了5000多元的彩礼。
在知青们的记忆里,边境寨子里的婚姻就像买卖一样。“现在不知道是多少钱,1970年代最贵就是1200元找个媳妇,其中一半给她娘家,一半买成筒裙。”当时在瑞丽插队的老知青卢进红记得,彩礼钱往往是双数,最多1200元,有的1000元、800元,或者更低一些。
5月的瑞丽,早晚的雨水和潮热提醒人们,这里已经是亚热带,距离缅甸越来越近。路边的芒果挂满树枝,肥壮的绿色覆盖大地,竹楼、榕树、蕉园、橡胶林,加上身材苗条的傣族姑娘,一派南国风光。
媒人“亮”的家,要经过一条仅够一辆小车通行的土路,这个叫弄别的寨子有89户人家,这里的傣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的生活方式,一栋栋砖房沿路而建,摩托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
亮的房子在周围砖房旁显得很矮小,手头并不宽裕的她,只能延续古老的建筑方式。狭小的竹楼里,亮坐在床上看着湖南台,发出阵阵笑声。忽然到访的陌生人,使亮的脸色沉了下来。
亮否认她欺骗原告,“在我们寨子里,缅甸嫁过来的姑娘多的是,但几乎没有跑回去的。”亮说,经过这件事后,她现在已经不做媒人了。
尹万桥的另外一名介绍人吞亮就住在喊沙寨子里,当地人告诉记者,像吞亮这种长期依靠做媒谋生的人在许多寨子都有,这些人一般找不到,他们多数在缅甸寻找愿意做新娘的女孩,然后将他们介绍到中国。而这些媒人更愿意将缅甸姑娘介绍到中国内地,因为那里给的价格会高一些。
2006年4月,河南省开始清理“三非”人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打工), 仅仅新蔡县就清查出69名缅甸妇女。跨国婚姻在我国内地非常普遍。他们的婚姻被定性为“非法婚姻”,这些缅甸妇女被全部遣送回国。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早在2005年,警方曾发现一条分工细致的贩卖缅甸妇女的交易链:一些人专在缅甸曼德勒地区一带找寻贫困妇女,以“到中国打工”为名,将她们诱骗到云南瑞丽市;“送货人”从“收货者”手中拿到酬金后返回缅甸;“收货者”再将她们带到昆明,转乘火车卖给中国内地山区的村民。
但媒人们的工作,到底是牵线搭桥,还是欺诈、贩卖难以界定。“一旦牵扯到中国内地,很多情况就不好说了。有的是媒人和婚托合伙骗钱,有的是媒人和内地犯罪分子勾结骗人。这些不仅仅针对缅甸妇女,边境一带的中国妇女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当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官告诉记者,此类案件,在边境一带时有发生。
中缅合作反拐瑞丽联络官办公室从2007年成立至今,共侦办重特大拐卖妇女儿童案件12件,抓获嫌疑人36人,解救并移交缅甸警方被拐妇女儿童135人。
“在弄别寨,因为吃4号(毒品)的人特别多,所以相对其他地方要穷一点。”喊勐也是尹万桥的媒人,她还有一个身份是寨子里的妇女主任。她说,中国姑娘因为彩礼钱高,一般都嫁到外省,或者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寨子去了。弄别寨子里的年轻人多数都找缅甸姑娘。
和尹万桥的不幸婚姻相比,在边境寨子里的缅甸姑娘,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性格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赏。“当然彩礼不能说成是买卖,媒人中介费也不能说成是买卖,这都是民间的习惯,必须要尊重的,但在广大农村实惠才是最重要的。”张向富是寨子里少有的汉族。他说,寨子里的姑娘嫁到外省去了,要是不往缅甸找的话,很多小伙子就面临着找不到媳妇的难题。
她们曾经是种植罂粟的能手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吴心灵陶醉在自己的歌声中,傈僳语赞美诗在这个景颇族村子里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在这座简陋的教堂里当众吟唱。
在一段长达26.8公里的边境线上,一条小河隔开了中缅,缅甸一边叫勐古,中国一边叫勐海,一座破旧的木桥将两个小镇连在一起。8年前,吴心灵就是淌着这条河找到了心上人,然后一直留在了勐海镇吕尹村。
吴心灵曾是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1998年,曹云德没有花一分钱就把这个缅甸姑娘娶回了家,这让今天的年轻人羡慕不已。
几年前,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勐古那边漫山遍野的罂粟花开,如今替代鸦片的甘蔗和橡胶林正在茁壮成长,虽然替代种植在近几年收效颇丰,但是毒品留下的后遗症不会在短时间被甘蔗或者大米所替代。毒品通过边境小道大量流入中国,毒品、艾滋病、赌博一直也困扰着勐海这个边境小镇的发展。
“我们前年人均收入1820元,今年的人均收入2335元,表面看着很高,但数字都是虚的。”勐海镇镇长张勒弄摇着头,尴尬地笑着。
“前面两年的禁毒形势非常严峻,村子里盗抢治安案件发案率非常高,自愿民兵护卫这项工作开展两年以来确实很有效果,卖毒品的不敢进来,吸毒的自然也找不到毒品。”勐海镇书记廖刚说,现在440名吸毒人员中,有148人实行了强制戒毒。
吴心灵、相潞们的丈夫很多走到了禁毒战争的一线,但尴尬的是,他们的妻子在嫁到中国之前,曾经是缅甸种植罂粟的能手。如今在中国,通过她们的方式,参与到了禁毒战争之中。
5月17日,基督教礼拜日,在村子中间,一栋简陋的白色土房子里传来的正是吴心灵的歌声,教堂外孩子们还听不懂深奥的圣诗,互相追逐、嬉笑。对于吴心灵来说,她希望自己的歌声可以感染更多的人,特别是那些吸毒的人。“有时候宗教比管教更有效。”吴心灵说。
“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新增吸毒人员,而是原有吸毒人员复吸率高达20%。”勐海镇书记廖刚说,这里一直是潞西市禁毒工作的前沿阵地,政府正通过各种办法降低吸毒人员的复吸率。
吴心灵的身份证来自缅甸,除此之外她已经完全融入了勐海,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她和多数中国妇女一样,喜欢电视里没完没了的肥皂剧,习惯把生了两个儿子的光荣挂在嘴边。
这个季节没有风,吴心灵将缅甸带来的老照片用镜框装裱,防止褪色,从家里照片出镜率来看,吴心灵对家中摆设有着绝对的控制权。最近她把母亲也接到了中国。这里的生活和缅甸完全不一样,充满了挑战。
和曹云德一样,岳三所也是民兵之一,他最近减少了礼拜的次数,他的妻子相潞刚刚从缅甸嫁过来,但相潞不得不忍受丈夫经常“上夜班”。“没有什么报酬,全是义务的巡逻。”岳三所是个黑瘦的男人,他看着相潞时,总是不经意露出会心的笑。
但随着农忙的到来,民兵的出勤率将在今后几个月里不断减少,这也是这场禁毒人民战争最尴尬之处。“我们是唯一的试点乡镇,但发动这么多的民兵参与禁毒,一分钱的资金也没有,过去两年里面我们就是这个单位要点,那个单位讨点,工作非常困难。”勐海镇镇长张勒弄不停地摇头。
没有结婚证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爸爸一个家,妈妈一个家,剩下我自己,好像是多余的……”10多年前一部叫《孽债》的电视剧在中国热播,故事讲述了上海知青在云南结婚生子,随后返城大潮到来,他们丢下了一批孤儿寡母回到上海。故事讲述了他们的子女长大后,进城寻找父母的尴尬过程。
周师傅是名老司机,他依然记得1970年代的德宏,知青充斥在每一个寨子里。每到周末,芒市广场上播放露天电影时,知青和少妇裹着从缅甸买来的军毯,一对对地坐在地上。“当时很吃惊,这种情况要是在内地的话,肯定是要犯错误的。”周师傅记得,当时的革委会为了控制此类事件出台规定:除傣族外,其它有类似行为的一律按反革命论处。但是知青们又转战到各个寨子里,“裹军毯”屡禁不止。
如今这条边境线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变成了机遇和财富的象征,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到此淘金,娶走了当地的姑娘,而当地的小伙子们又将目光转移到山水相连的缅甸。1979年之后,大量缅甸妇女嫁入中国已经成为事实,虽然记者并未获得这个准确数据,但缅甸媳妇们正在用她们的方式融入中国,除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融以外,她们渴望得到身份的认同。
与大量缅甸妇女嫁入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事离婚案件出奇的少,记者从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06年涉外离婚案例共2件,2007年1件、2008年没有。
离婚率少的背后,是结婚证几乎处于停办状态。记者走访3个寨子10多家涉外婚姻家庭,没有一家办理了结婚证的。“没有结婚证,法院无法受理任何他们的离婚案件。”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杨副院长说,同居与婚姻的适用法律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同居进行判决,往往对女方不利。
“我们没有结婚证,不知道怎样去办理。”岩思和缅甸女沙也已经结婚10年,有一个8岁的儿子,但他们和绝大多数嫁到中国的缅甸妇女一样,没有到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10多年前结婚的人,有的拿到中国户口了。但最近十年,边境新娘不仅拿不到中国户口,连结婚登记的手续都非常麻烦。”沙也说,自己的婚姻是非法的,说不定自己还会被遣送回国。
沙也8岁的儿子旺绿随父亲有了中国户口,但沙也由于是缅甸居民身份,她最远只能走到芒市。“想出去看看都不行,没有身份证,芒市有亲戚还能去一下,因为不用住旅店。”沙也很无奈,她只能每天守在这个边境线上。
80岁的缅甸妇女闷在中国定居了50年,但她至今最远只去过瑞丽市区,她的儿媳静同样来自缅甸,她结婚8年来最远到过芒市,因为没有中国身份证,她必须当天返回,“不然就只能住在街上了。”
去年,瑞丽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执法检查组报告后认为,“涉外婚姻带来的落户难问题是瑞丽市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缅边境上民间通婚的事实,形成了很大一部分缅甸边民已经多年生活在中国境内,但尚未取得中国户口的事实。这一部分人虽然已经变成了事实上的中国人,但由于其未依法律规定途径办理婚姻登记手续,因此,多年来也就一直无法取得中国国籍,也变成了现实中的“边缘人”。由此也给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时带来了重重困难。”
“你们一定要帮我们问问户口的问题,看什么时候可以落户?”离开寨子时,记者总会收到这样的托付。